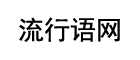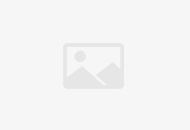优秀散文:家乡的石碾
过去,家乡村子大,分布在角角落落里有几座石碾,伴随着石碾的转动,曾为一方百姓带来过幸福,改善过生活。岁月悠悠,过去的石碾大多已不知去向,即使遗留下来的也浑身雕刻着岁月的斑驳,显露着历史的沧桑。
儿时碾米大多是在老屋附近一个半坡空闲处的石碾上,据说这是原来一个富户人家的,解放后归公了,附近的百姓用着就更方便了,白天整天不闲着,常见石碾周围围着许多人,一家接一家排着号,有时家数多了,都排到了晚上,索性挑灯夜战。有碾米的,有碾玉米面的,还有碾地瓜面的,有用驴拉碾的,用牛拉碾的,还有用人前边拉着,后边推着的。儿时曾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一起玩推碾,那时都是两家或几家合伙,有在前面把袢拴到碾棍上用肩膀拉着的,有在后面用两手推着碾棍的,还有用两手挎着碾框推着的,等有人说声:好了。用齐了劲,碾砣子就开始转动起来,就会听到碾砣子发出“呜呜”的声响,还有被碾压的粮食发出“巴嘎、巴嘎”的'声音,时间长了,这种声音听起来也就很自然了。刚开始碾粮食的时候,碾砣子与粮食间的摩擦力大,碾砣子特别重,推拉着很费力,慢慢地转着转着,就轻松了,等到碾得差不多了,碾砣子就变得轻松起来,发出顺畅的“咕噜咕噜”的声音,有时小伙伴们就会嘻嘻哈哈地推着碾砣子跑起来,在这种嘻嘻哈哈的推碾中,感觉不出有多累来,感受到的是一种欢乐。
石碾的东面就是一条小路,常见有上工、收工的、挑水的把这里走,见了相互说声:“碾米啊?”“哎,挑水啊?”“是啊。”打声招呼就过去了;石碾的旁边就是一个大姜井子,有几户人家在这里储藏大姜,等到碾米的高峰期和收大姜的季节,这里分外热闹,各忙各的,嘴里也不闲着,石碾的周围常常爆发出阵阵欢笑声,感觉推着的碾砣子也就轻松了许多。
石碾的西面坡上住着两户人家,在石碾与路之间,用乱石垒起一道矮墙,站在路上的人两肘刚好能放到墙上,这两户人家里的大人们都很热情,见了有碾米什么的,总爱探过头来打声招呼,有时还问:“喝水不喝?”“不喝,不渴。”就各自忙去了。有时遇着熟人,上面的就探过头来,脸向下朝着碾米的,两只胳膊趴到墙头上,碾米的则仰起脸,两眼望着上面的人,随石碾变换着不同方位,不停地说着话,因此石碾也演绎出许多的故事,延伸着街坊邻居的友谊,让乡村百姓灵动起来。
儿时记得,许多男女老少伴随着石碾走过,碾盘的下面已被踩踏成细土,圆圆的碾盘周围已凹陷了许多,这一圈一圈的足印,记载着强壮男人坚实的脚步,见证着欢快女人急速的步履,记录着上了年纪老太太的“三寸金莲”,留下了孩子们的欢快脚步,还有毛驴的脚步、牛的脚步……
如今,石碾已渐渐远去,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很难再见到老石碾了,现在反倒怀念起它来。我想,这是怀念那段留下的深情记忆吧。
碾子优秀散文
村里有两盘碾子,两个生产队一个队一盘。
碾房里一年四季忙碌,推碾子的人几乎每天挨饿。眼看就掀不开锅了,面黄肌瘦的孩子们不住地喊饿,年龄小的妹妹一阵阵干嚎。
邻居二婶家亲戚昨天送来半小袋歉熟的谷子,她给端来半升:“快给孩子们碾了吃吧。”于是,碾房里响起了咕噜噜的欢笑声。
碾房是村里最圣洁的地方,那是我们的粮食加工厂。
碾子由两块锨好的大石头组成。在一间房内用土垒起一个平台,然后将一块一丈方圆的平石铺上,这石上嵌好了有序的纹理,叫做碾盘。在碾盘中央钻有一个洞,上插一根铁棍,固定在平台上。在碾盘上,一块雕有有序花纹的圆柱石头用木框框住,以铁棍为圆周心,以碾盘一半为半径不停地转动,下面的谷物、豆类便被碾碎,这样反复多次,一旁母亲不住地用笤帚扫堆碾碎的东西,倒在箩子里,左右不停地摇,并不间断的拍打一两下箩子,不一会,她的头上、脸上、眉笔上都染上了一层霜,此时,箩下面的笸箩里的面粉也在不断地加厚。
“走,跟妈推碾子去!”妈的这一声喊给饥肠辘辘的我们随时都是一种莫名的兴奋。于是,箥箕、笸箩、箩、笤帚大人们套在一起拿,我背起一小袋豆类或小麦疯一般朝碾房奔去。
我们抑制不住兴奋,将碾棍插进束缚碡碡的木框的圆孔内,轰隆隆地一前一后追赶起来。这时很快被妈呵斥,没有粮食的空碾子最容易被毁,石头纹理的咬合会将纹理破坏。妈这时就说,空碾子推不得,来年要饿半年的。这又让我想起一句话,每逢我们在等不及饭熟,不停地用筷子敲碗,妈就脸色一变:“敲碗敲筷子,讨吃一辈子!”我们赶紧将碗筷放下。等妈用箥箕将粮食箥好倒在扫干净的碾盘上,说一声这回你们使劲推吧,我们吡牙咧嘴却难以启动那艰涩的碡碌。固定碡碌的木框有一前一后两个圆孔,成一平行的“一”字。这要两个人同时推才行。弟弟个矮,得抬起手抓住碾棍,我稍高一些,用胸口抵住碾棍使劲往前顶,推不了几下两人就气喘吁吁了。这时妈来替下弟弟,我也觉得轻松了不少。推完了一批,再倒新谷物的时候又是一阵艰涩,让人绝望。更主要的是这样重复机械的用力不一会就觉得泛味,全身是汗的我瘫坐在地上,眼冒金星,天悬地转。这时最盼救星来帮一下,因为我已实在没有忍耐力。
如果没有伙伴来帮忙,那最盼望的竟是驴。不过,那得有幸得到队长的允许。驴被牵到碾房,用黑布蒙上眼睛,再给它戴上笼嘴(防止它贪嘴吃粮食),给它套上碾棍,只要“得儿”喊一声,它就会奋然前行,周而复始,毫无倦意。偶欠也会慢下来,只要用小鞭在空中“啪”地一抽,那驴马上一个激灵,腰一弓,注意力绝对集中,又十分敬业地前行。这样一来,人是省了力,但伴随而来的却是遭到驴子内心的不满和发泄。时不时地,它会翘起尾巴,吧嗒吧嗒的拉下奶油面包一样的粪蛋,或者劈开后腿唰唰地尿出一股黄水。这时,整个碾房都会充满一股呛人的驴粪驴尿味,以后每吃饭时我老怀疑那浓烈的味道溶进了面粉里。
平时碾房要锁上门,以防谁家的鸡飞到碾盘上寻没有扫干净的米粒,那些笨家伙一点也不讲道德,时不时会将碾盘拉得满是鸡屎;还有那馋狗,见防备不严,就钻进碾房,蹦上去将碾盘舔个干净,令人作呕。平时,碾房比较清闲,但逢年过节这里就特别拥挤,尤其是到了年根,人们为碾那够一顿吃的糕面,往往一大早起来去排队,有人头天晚上就在碾盘上倒上一小碗谷物“占碾子”,但这还得不时防被谁家的狗钻进来当作一顿美餐。
邻村有一光棍刘大自小没了爹妈,一直靠邻里接济长大。他稍长大些,食量大,谁也养不起,他就走行串巷地给人说唱几句好话,或者诉自己的苦以讨口饭吃。后来,他觉得给人唱一些段子能换来一口好吃的,便东凑西凑拼成一些不成调的曲子。别看他人笨,连个四六句都说不好,一副竹板打来打去充其量也只是个道具,但人们教他一些荤调子,他倒悟性极高,没几天就背得滚瓜烂熟,能加油活醋的自由发挥,并且还能附加一些动作。随着年纪增长,有时,一些段子唱着唱着他就暗然神伤许久,三十大几了仍不知女人是啥滋味让他永远抬不起头来。他见男的就叫大哥,见女的就叫大嫂,有时见十六七的女孩子也叫,女孩子被他叫得又恼又臊,骂他不正经赶快走开。
刘大走村串户给人唱荤段子,成了村里一些成年人的'开心豆。人们为听他不断学来的新段子,除了让他饱吃一顿外,有时还夸赞他一番,他这时也会帮人们干一些小活。村里的女人便逗他:“刘大,唱是唱好了,可你亲过女人没有?”刘大一下子满脸酱红,嘴里嗫嚅到:“谁亲过唉——”“唉,白活了,你去找牛大姐吧,他肯定会让你亲一口的。”刘大半信半疑,经不住女人们的怂恿,刘大真也来了劲,问:“在哪?”“在碾房里。”牛大姐男人长年有病,孩子小不能帮忙,一个人推碾子实在不行,求人帮助,答应日后还工,但老这样也不是一回事。
来了劲的刘大真一路小跑来到碾房,见牛姐正一头白一脸红吭哧着一个人推碾子。刘大壮着胆子问:“她们说你想让我亲一口,亲哪里?”牛姐知道这是姐妹们开她的玩笑,也不恼,将脸往前一伸,一指右脸:“这里!”刘大上前就亲,却让牛姐用一根碾棍拦住:“你推那根碾棍,我推这根,多会你追上我就让你亲一口!”“当真?”“当真!”刘大这个卖力,前边有吸引力让他拼命追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可碡碌骨隆隆转得飞快,却就是追不上近在咫尺的牛姐。她喊牛姐你慢点,可自己却脚下生风,牛姐也跑得越快。“牛姐,你站住让我亲一口,我嗓子都冒烟了!”牛姐仍一个原则:“你追上我就叫你亲一口!”刘大就要崩溃了,眼见在跟前,就是够不着,明知不是梦,还是够不着。情急之中,他拔出了碾棍。这下没了阻拦,刘大跑上前去,抱住牛姐在她脸上狠狠咬了一口,染得他整个头脸都是白絮,这时他得胜一般蹦跳着奔去。
刘大也许对性太饥渴,加上成年女人拿他开心,或者有意的撩逗,使他有时也敢放肆。一日中午,一妇女正哄吃奶的小孩睡觉,刘大一进院子就唱起他的“讨吃调”。那女人在窗口用手往外摆了两下,意思让他悄些声,谁想这刘大理解能力太强了,以为女人那是让他“进来!”“进来!”他兴奋地冲进家里,单刀直入地问女人:“大嫂,炕上还是地下?”那女人操起笤帚圪塔劈头盖脸向他打来。刘大一脸的委曲:“这大嫂,不让就别让,打我做甚?”
如今,村里的两间碾房早已坍塌,那碾盘和碡碌也早没了踪影。各种标号的面粉看起来又白又细,但吃起来却是那样的寡而无味,远不如那从碾盘上收起来的面粉味道纯正,哪怕那面粉里面真的有驴粪味或鸡屎味。于是人们不住地感慨,吃着机器粉碎的精细面粉,再也吃不出拔出碾棍亲人一口的欢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