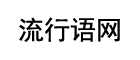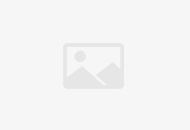朱天心的简介
朱天心写作起步极早,在北一女就读时就因《击壤歌》成名,大学毕业后专职写作。曾任三三集刊主编,其作品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等多项文学奖,现专事写作,为台湾文坛上重要的作家。著有《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昨日当我年轻时》、《未了》、《时移事往》、《我记得缮》、《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小说家的政治周记》、《学飞的盟盟》、《古都》、《漫游者》、《二十二岁之前》、《猎人们》等。
朱天文的评价
1994年6月,朱天文以《荒人手记》,摘取首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桂冠。实际上,这位出自传奇式文学世家的女作家,在其长达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早已数度领过文坛风骚。如由其为代表的三三体文学,曾在年轻学子中风靡一时。她与侯孝贤、吴念真等一起创作的电影《悲情城市》曾在威尼斯影展上获奖,掀起80年代台湾新电影浪潮。而使我们对她特别加以关注的,是她那呈现腾挪变化之势的创作,与20多年来台湾文学思潮的演变有着密切的感应,如她的作品在主题上的变化──从早期热衷于少女情怀的抒写到晚近集中于世纪末社会情态的观照──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台湾文学发展的某一方面的缩影。特别是从人文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看,其特殊的意义就更为凸显。朱天文的早期作品,大都以年轻学生的校内外生活为题材。它们的第一个特点,是十分生动、真实地写出了正值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女的微妙心思,塑造了秀外慧中、率性真诚的年轻女子形象。除了多愁善感、情思细腻等普遍特点外,朱天文还写出了许多带有私密性的少女情怀,如自恃年轻漂亮的骄矜,对有竞争力女友的妒忌,担心辜负青春的怅惘,无缘无故地生气和想要自杀,为了体重增加一公斤而发誓不再吃巧克力,人长得好看,到大学来,更是以为每个男孩对自己有意思的自作多情等。其中最特别的,是袒露了作者对于不少年轻男子的倾羡、爱恋之情。如对好几位任课的老师,作品中的我都有过近乎暗恋的好感。《记得当时年纪小》一文中写道︰陈天音老师的课,我爱他的薄嘴唇,就决心把报告来做好;大四选修中文系的杜甫诗,不为杜甫,为教杜甫的张之淦老师我喜欢。除了年轻老师外,作者与之情深意笃、情意绵绵的男同学也有不少,甚至连女友之间也有类似恋人的情谊,如想要对仙枝托付终生(《陇上歌》)。由此可知,朱天文所写,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友情,是如清泉般沁人心脾的常人之情,诚挚的待人之道,一种贾宝玉式的施予广泛而又不落色境的天生情种(《俺自喜人比花低》)般的爱。朱天文的这种泛爱,其本质是一种对生活生命充满热爱、对自然万物心怀感激、对世间百态给予宽容的真性情,而它所否定的,是那种缺乏情调和诗意的道学气。如《贩书记》中描写不为爷爷所欣赏的男生,尽管懂得不少学问,却令人觉得他气息不通,原因就在这男生没有诗意。爷爷称︰当着年轻姑娘讲话,那言词举止之间总该有所不同罢,但是这男孩居然能视若无睹,可见是个没情调的;学问无论做得怎样高深,如果没有性情,便仍是身外之物,到头终归一场虚妄。一切学问,必是诗意的才是真学问。这或许可以解释朱天文格外注意写出生活的诗意和性情的原因。朱天文珍惜、感动于友情,从殷殷友情中感受到人世的幸福,从而对生命抱持着知恩图报的感激心理,而这又源于一种年轻的喜悦,生命力的飞扬。作者对于生机勃勃的事物有着大欢喜,而这种生命力体现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和对陈规陋习的突破。因此朱天文称︰我喜欢危险这两个字,因为危险才是青春永驻。(《写在春天》)《贩书记》中描写虽然卖书的实际成绩并不佳,但大家并不为事情本身的成败得失所囿,特别是妹妹天心,卖书成绩最差却兴高采烈,这种对将来无缘无故的喜悦,真是非常年轻而明亮的糊涂。同时由于太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了,因此连这个世界的败坏和沉沦都不忍舍弃,还要眷恋,还要徘徊(《怀沙》),其实乃是因为有好有坏才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人间的至情至性。正因为如此,朱天文表示︰我宁可做一个世俗热闹的人,也不做圣女(《我梦海棠》)。朱天文还进一步将此种率性真诚和生命力的飞扬上升至民族传统文化性格和审美特征的高度上。作者毫不掩饰她从古书、史书中受到传统人文精神的熏染。她写道︰我们读经书的心情,也是好像面对亲人讲话,是我们的祖父忽然来到眼前,见着了他的人,就是见着了历史的绝对信实,也是见着了生于这历史里的民族情操。(《仙缘如花》)她宣称︰我爱古诗源,我爱里头的世界永远是这样高旷亮丽的。(《有所思》)她也从民俗中感受中国人丰厚的人文气息︰想着中国的婚姻,真是从一片广大的人世里生出来的,而新式的婚礼……没有深广的人世为背景,等情感如烈火燃烧完了,就真是完了,那场面的单薄实在令人气短。(《之子于归》)作者更从自己的家庭中亲身感受一种自然适意的氛围︰我四周的一切好像都是没有名分的,父亲母亲做的不像父亲母亲,我们做子女的不像子女,即与人家恋爱也不是回事,倒像是海边玩沙的一群孩子,玩玩忘记其所以,太阳、月亮、星星统统落到浪涛里去了。(《我梦海棠》)而爷爷的告诫︰首先要把身上既有的障碍撤除,以赤子之心才能和万物素面迎接(《仙缘如花》),更使传统人文精神落实于可感可触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得到体现。朱天文以此与西方现代社会相比,指出︰美国人在产业经济的袭卷之中,已是根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还有情意这件东西了;而且美国式教育最伤害人的地方,就是隔绝了人对人对物的感激之心,一切都落在科学的方法论上,变得人越来越没有感知的能力了。朱天文早期作品以描写真性情为主要内容,而其艺术形式也是与此紧密配合的。它们不求悲剧性的冲突,也不求故事情节的曲折,而是立足于表现正常生活中正常人所发生的正常事件(《我们的安安啊》),着笔于琐碎的生活细节,透过它们写出人的性情,特别是少男少女们的生活情趣。这一特征,与张爱玲的影响不无关系。朱天文很早就心仪于夏志清所概括的张爱玲小说的风格──苍凉。据朱天文所理解,苍凉不是强大的悲壮,悲壮后面的情操是可名目的,而苍凉是在力量的背后有着荡荡莫能名的情操,它并非如龙卷风的旋律,而如东方式的击磬的音调,一击是一个单音,像露水涌落湖心,清风徐徐的吹开涟漪,似乎连续又似乎不连续,有时上下不关剧情,照样好得不得了,无损于戏的完整性(《看〈江山美人〉》)。此外,张爱玲提供了一种观看世界的直观方式,不靠手段、逻辑,不靠知识、学问,理直气壮地写她所看所想的,以一种比较自然生成的态度从事创作。这种特质,对很年轻就开始写东西的人来说,似乎都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因为年轻不更事,既缺乏人生历练,又读书不够,但只要心眼剔透,感觉敏锐,就可以放胆写尽一切琐碎和曲折。这也是所谓张派。当然,尽管出手亮眼可喜,却因此耽溺其中,难以超脱,甚至成腔,就令人烦(王之樵︰《如何与张爱玲划清界限──朱天文谈〈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中国时报》1994年7月17日,第39版。)。这可说道尽了朱天文早期创作的个中奥秘。如果说台湾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着重表现特定时代氛围下放逐者内心刀搅的焦虑,负载着极为沉重的哲学思索和使命感,70年代的乡土文学着重揭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立足于为贫苦阶级申言,那朱天文及其三三派却以着重对人的真性情的描写、表达生命的喜悦和欢欣、以及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吸取和弘扬,显示了与上述二者颇为不同的人文主义的创作风貌。从1983年起,朱天文开始参与电影文学创作,标志着她的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时她跳出了较多描写私密性少女情怀的限囿,对现实社会有了更广泛的涉及和观照,如与吴念真合作的电影剧本《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然而,即使是这些作品,也仍一脉相承地保持着前期创作的某些特征和倾向。其中最明显的,即是对人的生活的兴趣甚于对政治和历史的兴趣。这正如张诵圣所概括的︰这群作家始终以人道精神的角度来看待个人的生活;同时他/她们一向以个人而非社会政治的观点去了解历史。如《悲情城市》表面上看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其核心主题却是历史如何侵犯了不涉政治的平凡人生活的故事(张诵圣︰《朱天文与台湾文化及文学新动向》,《中外文学》第262期,1994年3月。)。它并未特意凸显献身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者所受的迫害,相反地,它描写的若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物,便是因生理缺陷而无法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者,这和陈映真同一时期的类似题材作品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而且这种倾向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在《悲情城市·序》中,朱天文写道︰当我们逐渐跨越出生存的迫切性走出一个较能活动自主的空间时,关心的焦点自然也不一样。除了向来非杨即墨的派别之争,路线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似乎还别有一块洞天可以拿来想象,思考。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中,朱天文又写道︰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地带,那里,各种价值判断暧昧进行着。很多时候,辩证是非显得那么不是重点,最终却变成是每个人存活着的态度,态度而已。作为编导,苟能对其态度同声连气一一体贴到并将之造形出来,天可怜见,就是这么多了。(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三三书坊1989年初版五刷,第29页。)所谓写出每个人存活的态度,与早期作者致力于写出人的真性情的努力,显然一脉相通。朱天文的早期创作中充满了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赞美感激和对青春与生命的礼赞︰生命是这样的华丽喜乐,过都过不厌。但是到了《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等近作,充斥其中的却是一种老去的声音(詹宏志语),一些食伤了的欲望,一种对生活的厌倦和无奈,一些人际关系的隔膜和疏离。如《带我去吧,月光》中的母女俩因感情创伤而双双得了失忆症和恹睡症。《肉身菩萨》中同性恋的主角三十岁已经是很老,很老了……生命流光,身体里面彻底的荒枯了,脸像有层盐霜,看起来好像跟每一个人都有仇,成为一具被欲海情渊腌透了的木乃伊。《红玫瑰呼叫你》中的翔哥40岁不到已呈老状和性无能,并预见自己会在老婆与儿子们用他完全不了解的语言交谈中不断猜测,疑惧,自惭,渐渐枯萎而死。《世纪末的华丽》中的时装模特儿米亚,不断更换的华丽的衣装内,却是一颗空无、寂寞、苍老的心灵──20岁已不想再玩年轻人的爱情游戏,找了一个40多岁的有妇之夫同居,而真正能够患难与共的只有那些日见枯萎的风干玫瑰。《恍如昨日》中行遍宝岛无敌手的演讲家的隐忧在于︰汲汲于浩繁新知,知讯异变为欲望黑洞,全部投入也填不满,他已有点食伤了。高素质优裕生活的深暗层,他隐隐恐惧有朝一日会透透倒味掉连字纸也不看时﹗将这些收于《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短篇小说合起来看,其展现的正是当前台湾都市社会诸般景观。它带有无深度、无历史感、消费膨胀、人欲横流、理想破碎、复制和假冒泛滥等后现代乱象,也呈现着颓废、厌世、隔膜、腐烂等世纪末景致。如果说这时朱天文的小说创作,其以人的生活和性情为描写焦点的特征仍未改变,但其反映的生活内容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转变,固然因作者年岁渐长而自然地告别了青春写作趋于社会观察的深邃厚重,同时更缘于作者对于台湾社会转型、时代变迁的敏锐感应。正因为如此,朱天文小说的变化才能反映了台湾文化及文学新动向(张诵圣语),同时也代表着台湾战后新世代小说家创作的新取向。当然,与其它致力于描写后现代社会状况的作家相比,朱天文仍有其比较特殊的视角。如张大春主要对信息传播环节加以审视和质疑,林耀德主要描写信息时代的都市社会景观和人的心灵特征,朱天文则似乎更多地从情与欲的角度加以表现。这一点,在其获奖长篇小说《荒人手记》中有更明显的表现。《荒人手记》以一男性同性恋者自述的口吻,展现这一社会畸零族群的爱欲生活和孤独、寂寞的内心世界。他们感染长年不愈的游离性、无根性,精神上早就塑成了拒斥公共体制的倾向,往往未败于社会制裁之前倒先败于自己内心的荒原。由此也可知,作者写荒人(遭社会遗弃或遗弃社会之人)的意识更甚于写同性恋者,她乃借同性恋这一极具代表性的题材为社会边缘族群、乃至整个现代人群作心灵的写照。作者笔下同性恋者的欲情世界,也和常人世界一样,呈现光谱式的多样色彩︰有刻骨铭心之爱,也有嫖与被嫖的商品买卖行为;有精神恋爱式的雅士,也有移情别恋的负心郎。其中颇令人玩味的,是费多这样的自恋的洁癖症候群。这是笼罩在艾滋和臭氧层破大洞底下长大的新生代,他们宁愿干干净净自慰,也不想跟人牵扯欲情弄得形容狼狈。他们不想当gay,因为太麻烦。他们要一种绝对舒服无害的植物性关系,清浅受纳,清浅授予,要避免任何深刻,惟恐夭折,因深刻具有侵蚀性,只会带来可怕的杀伤力。他们的这种新的性观念,典型反映出社会的后现代特征。但她早期就已形成的一些创作特征,如着重个人真性情的表现而轻忽历史与政治的涉入,推崇感性而排斥理性和学究气,擅长细腻的细节和华丽词藻等,朱天文文学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自身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情趣盎然,感性充溢,文采熠熠,别有一番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