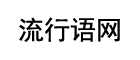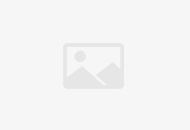金陵十三钗影评
对于金陵十三衩,我并不陌生,因为在它刚刚上映的时候,我就已经体验了其中的彻骨心酸。今日坐在教室里,再一次的回味震撼。一个动荡的年代,人心惶惶,无从逃离的恐惧,该如何去面对,该如何去铭记。真正的,看着大屏幕,深一些,如果我处在其中,我想对那满目的疮痍,我只会感到无力了吧。人人都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对于这个年代的她们,近日网上的新诗应该更能道的真切些,商女熟知亡国恨,赎幼之身永贞真,山崩地摧志犹在,兴我中华休忘魂。兴我中华,休忘魂,魂,这是一个带着尊严与信念的载体。整部影片,阴沉抑郁,灰暗的整体色调,看着就让人揪心,想着那里,人无安逸,恐惧扎心。小的时候,还记得在美术课上的水彩课,在多么美丽绚烂的色彩上,只需一点黑色加入其中,他便蔓延开来,腐蚀着多彩。但是,在一片黑色之上,多少亮丽的色彩只是转瞬即逝,刚刚延开的触角一眨眼便淹没在一片黑色之中,沉了下去,永远不会再起来。她们,一群拥着色彩的女子,被那一双双暗淡的眼睛透过美丽的窗子凝望着,有欢声飞扬,有笑语回荡。为了这群孩子,她们失了色彩,掩埋了,在这炼狱般的世界。金陵十三衩里包含着与以前电影一样的情感,爱国,奉献。中国人,很伟大,或者,人都是伟大的,在一个场景中,一段年代里,一波,又一波的涌现。教堂,在那么一个满是流血的土地算是一方避难之地了吧。外出却受死的她们,到底为了什么,琵琶弦,亦或是耳环?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她们也愿冒死而寻,处在世界的边缘,在边缘有如何呢,战火还是烧到了她们。当她们乔装学生,那怀中的剪刀,是她们赴生死之约的武器。一直记得在地窖里,她们的光彩,那般夺目,她们的歌声,虽然穿着朴素的学生棉衣,但那首透着苍凉凄美的秦淮曲,直到现在,任在心中,每每想到在一方小小的地窖里,却飘浮着多少的侠义真胆与真情心语,眼湿了,心碎了。现在幸福生活的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对那惨绝人寰的场景最多只有哀痛,难以置信,生活前进中,人也慢慢忘记了哀鸣的痛楚。只盼全世界能平安永世,此般地狱的世界只存在于过去,放眼未来,是拉起的友好之手。
金陵十三钗影评
《金陵十三钗》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影片,故事发生在这场史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中,讲述的是南京沦陷时期一位美国殡仪师约翰无奈之下冒充教父,与一群躲在教堂里的学生、十四位秦淮歌女以及国军士兵之间为了相互救赎而在危机中自我牺牲的战争故事。该影片从独特的角度进行叙述,不同于以往战争影片的是在《金陵十三钗》中描写战争的场面极少,但它所带给观众的沉重感却是不容小觑的,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在残酷中散发出别样的真实和震撼感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影片,与其他主旋律电影不同的是《金陵十三钗》中没有强大的主角光环,影片以一群边缘人物构成主要角色,导演在人物的塑造上给观众带来了一个个丰富细腻的人物形象。影片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深入的思考,从色彩,声音,语言,镜头,人物与主题上都是一部具有特色的优秀电影,让文化穿越时空的限制重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不仅回顾了历史也引起了深思。
高分悬赏。金陵十三钗影评,要求原创的专业一点的影评,谢绝东拼西凑的东西。
中国的抗日叙事已经汗牛充栋,《金陵十三钗》的突破在于人物谱系的多元化,在这部影片的肖像学图谱里,能够看到多国电影二战叙事的基因,也能看到以往抗日叙事的延伸和进化。创作者花费心思利用既有的肖像学传统,颇为讨巧地将种族、阶层、性别等多重冲突编织在一个关于反抗与拯救的故事当中。最难得的是,叙事折射出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现代性状况,这一点恰是以往很多抗日叙事所忽略的。
《金陵十三钗》以一名白人男性作为主人公,将故事空间设置在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教堂,两组对位的女性人物——女学生和妓女,分别以教育/正途和商品化/邪路的方式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她们的现代性体验因日本攻入南京这一灾难而中断了,这恰是中国国家命运的缩影——初具雏形的现代化进程被侵略战争破坏,在当时唯一能够依赖的便是居高临下的盟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男主人公。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次现代性创伤,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状况有意无意地通过二战叙事反映出来。相比之下,中国大多数抗日叙事往往带有浓厚的“前现代”痕迹,是千篇一律的“复仇叙事”,运用的是一套高度本土化的肖像学,英勇的游击队战士、凶神恶煞的鬼子、农村空间等等,与其它国家的二战叙事没有构成有效的呼应和交锋。近年来《南京、南京》、《风声》、《拉贝日记》等影片试图跳脱这种模式,开创新的肖像学传统。与之前的尝试相比,《金陵十三钗》的话语模式是更为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通过详细梳理该片的肖像学谱系,能够发现本片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二战叙事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恰是建立在国族现代性体验之上的。纵观世界各国的二战电影,将女学生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叙事模式在反法西斯阵营的电影中并不多见,反而是战争加害国日本津津乐道的主题。最典型的便是“姬百合”神话,《姬百合之塔》(1953)是日本战后最著名的反战电影之一,由今井正导演,水木洋子编剧。自1953年之后,曾经多次被搬上银幕,除了1987年今井正自己重拍的版本,还有1962年版、1968年版、1995年版、2007年版等等,每一版都启用一批当时代最受欢迎的少女偶像们来出演。故事讲述了美军登陆冲绳时,一群冲绳本地的女学生被军方组织起来,称为“姬百合部队”,与军队一起行动,承担医护任务。在美军和本国军队的双重威胁之下,女学生们倒在了冲绳的海边。今井正的版本创造了一种“无辜者叙事”模式,将主人公们作为纯洁的化身,看着这些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少女,被战火无情吞噬,人们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怜惜之情,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金陵十三钗》中的教会女学生与《姬百合之塔》中的女学生年龄相仿,形象也略有相似,可以放在同一个肖像谱系中来比较。《姬百合之塔》中的女学生是单质的、平面化的,她们作为一个整体,除了最核心的主人公(也是最重要的少女明星),几乎分辨不出个体。《金陵十三钗》亦然,比起风姿各异的妓女群像,女学生们显得面目模糊,连主人公书娟也不甚清晰,她们的蓝布长衫和“姬百合”们的水手服具有同样的符号功能,是战争年代纯洁无辜的受害者的标签。女学生身份究竟负载了怎样的文化意义?为何在日本二战叙事中如此盛行?中国电影此番运用女学生形象,与“姬百合神话”蕴含的创伤感是否有共通之处?《姬百合之塔》反复强调女学生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细节包括她们在战火中举行了毕业典礼;她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自己关于英国经济的研究手稿;在生命的最后一夜,少女们唱的歌曲是《故乡》(《金陵十三钗》中日本军人也唱了同一首歌),歌词诉说的是在外求学的游子对乡土的怀念,流露出一种典型的明治意识形态,即为了追求现代文明和进步,远离故乡,功成名就之后内心泛起怀旧之情,这种意识与片中少女们的身份是符合的,她们是现代人/文明人的代表,代表着“正常的”现代化途径(教育),而军人代表着以战争为手段的“非正常的”现代化。《姬百合之塔》并没有强烈指责敌人/美国,灾难的主要责任在于陷入非理性狂热的本国军队,这符合日本战后的主流观点——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因为军方的孤注一掷而血本无归。再看《金陵十三钗》,书娟们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会说流利的英文,演唱赞美诗,她们不同于以往抗日叙事中的中国受害者形象,日军“三光政策”下的农村受害者们完全是前现代的,而书娟们是中国初萌的现代性的象征——脆弱的、容易夭折的,必须依靠西方的扶持才能幸存。书娟的父亲会说英文和日语,可推测出其买办身份,其他少女们的出身很可能与之类似。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阶层推动的,因为其浓重的殖民地色彩,在以往的抗日战争叙事里,相对于农村底层民众,这一阶层的状况往往被忽视,直到近年,人们才开始重新评价洋行买办们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样作为纯洁无辜的战争受害者,“姬百合”和书娟们都隐喻着本民族“正常的”、渐进的、改良性的现代化进程,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女学生是日本现代教育制度的受益者,虽然教育模式学自西方,但已经经过了日本式的改造,这与日本战时的现代性状况是一致的。西方势力已经被驱逐出境,“姬百合”神话中只有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教师/日本知识分子,并没有西方异族导师的存在。而书娟们要直接依靠西方文明的代言人约翰,与当时贫弱的中国无力抵抗日本,必须仰仗美国援助的状况相符。将两组女学生对比,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落后于日本的事实,两国同时期不同的现代化状况决定了,“姬百合”们把西方看作敌人,书娟们把西方视为拯救者。然而除去这一差别,当东亚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选择女学生作为战争创伤载体时,无形中印证了一种共同的现代性体验,无论先进后进,东亚的现代性不可避免暗含着对西方的从属和仰视,代表东方的不是成熟的男性,而是未成年的、学习中的女性。女学生代表着靠西式教育培植出的现代性,这是社会中上层的特权,妓女们则象征着底层的现代性萌芽,她们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方式是将自身商品化。比起被西方的文明传播者/教会(神父)以西方女性为模板塑造成型的女学生,妓女们的现代性是自发的、杂糅的、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正如她们的兼具东西方特色的外表:烫发、胸罩、丝袜和旗袍、琵琶。西方拯救者/约翰看待女学生(书娟)和妓女(玉墨)的眼光是不同的,书娟们与西方的少女在约翰眼里没有本质的区别,她们是单质的、纯洁的孩子,“无性”的天使,绝对的“善”的化身。妓女们才是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殖民地风景,阴性的、色情化的,是白人男性的欲望对象。女主人公玉墨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曾经是一名女学生,她是近代中国两条并行的现代化路线的交汇点,她流利的英文和风情万种的举止将两个群体的特质熔铸为一体,是最能满足西方幻想的东方形象。与西方流畅沟通的能力和异域女性的神秘魅力,且作一番不甚恰当的联想,当年宋美龄游说美国国会支援中国抗战,不也是凭借类似的特质吗?仗义舍身的妓女形象已经成为战争叙事的套路之一,因为性放荡而遭社会共同体鄙夷的女性,通过献身拯救“纯洁的”女性而洗脱了道德污点,成了撒玛利亚式的“圣妓”。只要涉及战争中的性暴力,该桥段可以为任何国家的战争片所用,中国抗日叙事中的例子有《南京,南京》,日本电影中亦不乏献身苏联军队,拯救满洲移民妇女的慰安妇(如《人间的条件》、《流转的王妃》等),或慰安妇在日军侵犯战地护士时挺身而出的情节(《听,海神之声》)。“圣妓”桥段背后的逻辑是对个体社会价值的测算,在贞节的妇女与堕落女性之间进行权衡,《金陵十三钗》在此基础上引入了阶层和文化地位的差异,约翰问陈乔治:“一边是女孩,一边是女人,两边如何选择?”约翰代表了本片的观点,默认了如此测算的合理性。他尽管爱慕玉墨,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两股现代性潮流之间,“女孩”代表的“正常的”现代化是更值得拯救的,她们作为西方亲手栽培的现代性萌芽,有待成长和发展,是落后国家重生的基础。而“女人”是如杂草一般任意生长的畸形的现代性产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颓废性的缩影,只有通过自我牺牲实现其建构性的价值。通过刻画女学生和妓女从冲突到和解的过程,阶层之间的矛盾被弥合了,呼应着抗日战争对中国民族共同体产生的凝聚作用。本片中的中上阶层是西方化的,而底层更具东方色彩,女学生说英文,唱外国赞美诗;妓女们说色情笑话,唱江南情歌小调。中上阶层的禁欲与低层的纵欲构成了反差,女孩对女人既鄙夷又嫉妒,那种成熟的女性魅力是她们尚不具备的,和解呈现为对彼此文化价值的肯定。妓女们通过裹紧胸部、拉直卷发、洗尽红妆实现了和女学生的同化,进入了由中上阶层垄断的“正常的”现代性状态,想象着母亲看到自己成了“读书人”该有多高兴,弦外之音——为了重归纯洁和身份提升,牺牲性命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已经高度西化的女学生从妓女身上看到了民族传统文化之美,原生态的传统往往来自民间底层,她们用心聆听《秦淮景》,回忆着女人们一身红妆拥入教堂的情形。这一刻上层与下层的现代性融合了,女孩和女人共同象征着彼时中国的时代状况。日本二战电影中也有一类代表底层现代性的人物——战败后专门以美军为服务对象的妓女“潘潘女郎”,玉墨们在服饰造型上和日本电影里的“潘潘”颇为相像。日本战败之前,西方文明一直是由上层精英引入,自上而下向民间渗透,这种西方化是经由统治层精英提炼改造过的。当西方文化以占领者的姿态直接出现在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空间里,潘潘成了西方文化在底层和边缘的代言人,通过她们,西方化向主流和中心渗透。《金陵十三钗》肯定女性以身体为资本求助于西方男性的行为,象征意义上,中国求助甚至乞怜于西方是现实情势所需,实际上也得到了西方的同情和怜悯。而日本眼中的二战是与西方的对抗(亚洲战场的侵略行径被刻意遗忘了),潘潘们代表的“非正常”的西方化是无奈而屈辱的。实际上,在东亚这一非西方世界当中,以妓女为代表的底层现代性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被否定的,人们更希望以“女学生”的方式实现现代化,《金陵十三钗》的策略是让妓女与女学生同化,而日本电影中的潘潘则堕落到底。男主人公约翰是来自西方的拯救者,也是成熟的现代文明的化身,与女学生和妓女代表的前现代国家尚未成熟的现代性萌芽相对照,他修理卡车/现代文明符号的行为也佐证着这种身份。约翰属于大屠杀叙事中的“中立者”谱系,如《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拉贝日记》中的拉贝、《再见,孩子们》中的神父,乃至《卢旺达旅馆》中的旅馆经理,他们要么属于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国家,要么从事商业、医生、宗教等相对不受政治影响的职业,这类人物的身份便于周旋在屠杀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他们表面上是“中立的”,暗地里为弱者提供某种庇护。《金陵十三钗》中的约翰与辛德勒类似,他经历了从普通人到英雄的蜕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异族女性的本能欲望起到了推动作用,纯洁无辜者的惨死则唤起了人物心中的人道主义情感,《金》片中摔死在约翰面前的女学生与《辛》片中的红衣小女孩有类似的功能。这种“普通英雄”是很讨巧的叙事套路,自私、放荡等缺点反而让主人公的拯救之举更有人性光彩。值得注意的是约翰与中国女性们的关系,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活跃各地的游击队,主战场的正规军主要依靠美国扶持,这一点在中国的抗日叙事中很少被强调,《黄河绝恋》中虽然出现了美国飞行员,但他与中国女游击队员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平等的,算不得对战时中美关系真实状态的隐喻。无论如何评价《金陵十三钗》中“依靠西方获得拯救”的叙事内核(也是《拉贝日记》的叙事内核),不可否认该片是对于战时中国与西方关系更准确的影射,中国城市中上阶层的现代性是西方一手扶持起来的(以教会学校为代表),西方援助中国国民党/中上层(而非共产党/底层)反抗日本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日叙事大多数描述共产党的游击战,叙事空间以农村为主,国民党、主战场、城市、西方等元素被屏蔽了,抗日神话的主题是中国民众浴血奋战驱逐了日本侵略者,仿佛没有依靠任何外力,这与日本的主流观点正好相反,日本至今不愿承认被中国打败,向中国投降被视为输给美国的后果之一。在日本保守倾向的二战电影中,时不时鄙夷地提到中国躲在美国的裙子底下,且不理会日本保守派的极端言论,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战时依靠西方“盟友”是现实的出路,《金陵十三钗》难得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并将之合理化。《金》片中,玉墨利用色相诱使约翰相助,但在两人的交锋中,她始终掌握主动,并没有丧失尊严。当约翰暴露出他心灵最柔软的一面,告知玉墨他为了给死去的女儿化妆才从事殡葬人员的职业,他此时已经从好色的、唯利是图之人,蜕变成了英勇的、人道主义的拯救者,玉墨委身于他的行为有两情相悦的成分在内,不再是赤裸裸的肉体交易。通过这套叙事策略,《金》片通过白人男性/成熟的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女性/未成熟的现代性萌芽这一图式,影射了战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同时又竭力淡化中国仰承美国鼻息的弱势地位。本片中的日本军人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野蛮暴力的底层士兵,一类是相对文明的军官。前者在中国抗日叙事中屡见不鲜,而后者很少出现。如果看其他国家的二战电影,会发现许多彬彬有礼的“敌人”形象,如美国电影《钢琴家》中弹钢琴的德国军官、《虎,虎,虎》中的山本五十六、《硫磺岛来信》中的栗林中将、法国电影《海之沉默》中倾慕法国文化的德国军官等等,包括今年日本电影《太平洋的奇迹》中的美国军官。在当下流行的战争片话语中(尤其是和平主义和反战话语),过度妖魔化敌人的处理方式显得呆板,人性化的敌人更利于表达战争的复杂性,这并非简单地美化敌人,有时是借敌人来肯定己方的价值观,有时是为了揭露敌人人性外表下的异化本质。中国战争片的状况与民族情感记忆有关,作为被压迫和欺凌的弱国,战争被视为民族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彰显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的舞台,残酷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人的感情记忆中没有“反战”的土壤,“人性化”的敌人是很难被接受的,《南京,南京》就是例证。《金陵十三钗》中出现了一位貌似有“人性”的军官,日本军官长谷川会说流利的英文,尊重神职人员,能够弹奏风琴和演唱歌曲。如果对日本战争片有所了解,便会发现这套塑造人物的策略借鉴了日本电影对本国军人的画像。在战后的日本电影中,普遍存在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上层的军官更像是武士,气宇不凡,有高贵的尊严,参与的残暴行为较少,因为那样将有损武士的德行;相反,下级军人常常胡作非为,欺上瞒下,虐待新兵,滥杀无辜,与日本古装时代剧比较,会发现他们的形象并非武士,而是时代剧中猥琐、自私的农民。通过这样的转化,日本战争电影将战争带来的屠杀和残酷,归结为参战者个人素质和品德的问题,战争的罪责被个人化和偶然化了。
急求金陵十三钗,要写影评什么的,谢谢
导读:张艺谋的最新电影《金陵十三钗》已经上映,大家热议不断,不管是影片的主题还是演员都已经盖过了《龙门飞甲》,国内对《金陵十三钗》的影评好坏参半,而外国人是怎么看到这部电影的呢?《好莱坞报道者》写了一篇标题为一团揉着妓女、修女和假牧师令人难以置信的纱线的《金陵十三钗》国外影评,对张艺谋的这部电影评价极其低。
《金陵十三钗》国外影评:一团揉着妓女、修女和假牧师令人难以置信的纱线
好莱坞报道者》首席影评人(Todd McCarthy)撰文评论对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产生了质疑。该影评不但没有延续此前《金陵十三钗》好评如潮的口碑,对《十三钗》评价极低,票房前景看淡,而且全文充斥着对故事真实性和可信度的指责。下面就来看看《好莱坞报道者》版的《金陵十三钗》国外影评。
【只有最粗鲁的好莱坞制片人才会想得出来这种奇招--在南京大屠杀如此阴森可怕的事件中注入性幌子--但这就是《金陵十三钗》的中心元素,它是对于一个经常被戏剧化的历史瞬间一个过份算计的、毫无说服力的再创作。作为中国全资的率先启用美国明星的电影之一,张艺谋精心制作的阵容豪华的电影由于贝尔的出现无疑会吸引眼球,但是它还远不如陆川导演用同一事件拍摄的《南京!南京!》,它在北美的商业前途看来十分有限(暗淡)。
为了让观众更容易走进故事,电影有意让一个政治上没有信条的美国人走入一群绝望的由教会学校女生和妓女的市民群体。电影从南京失守后的1937年12月13日开始,一群女学生从温切斯特教堂找到了临时避难所,得以躲避疯狂施暴的日军。同样藏在那里的是个孤独的美国人约翰米勒,他的大胡子像60年代的嬉皮士,他的行为举止甚至对话同样显得愚蠢而且不合时代。用一个中国人描述他的称谓最为恰当,那就是蠢驴,当无时无刻不自私透顶的米勒扫荡私藏的红酒、索要毫无根据的钱财时,人们不禁会问,也许有许许多多动机把一个白人描写成愚笨的钱财的奴隶,当然独在异乡为异客意识形态上没投入的美国人是个标准的电影人物设置,卡萨布兰卡里的里克就是一个最令人难忘的经典。但是贝尔离那个标准相去甚远。
很显然,从戏剧设置来说米勒需要这样的低起点来完成他从以自我为中心的醉鬼到高贵骑士的转变与升华,可惜的是无论是剧本还是演员都未给人物角色提供任何实际或者生造的人物背景前史,他确实为他所目睹的震惊,但是上几个礼拜他在哪(难道他是外星人)?这个角色没有带来任何观点或者洞察力,他只是个等着被填满的空瓶子。
同样找寻庇护的是当地妓院的十三个花枝招展的妓女,好像是要即将登场唱《花鼓戏》的一个大合唱似的,那些叽叽喳喳的妓女推开那些战战兢兢的女学生把避难所当成了自己的家。米勒以为自己撞了大运,立即对其中最傲慢的玉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玉墨一边吊着心急火燎的米勒胃口,如果你帮我,我就会前所未有地报答你,所有的人都会。帮人的前提是日本人不会动西方人。米勒从混蛋到圣人的不经意的转化源自他穿着的教士僧袍无意间阻止了闯入教堂寻找花姑娘的日军。看到了这个便利,米勒剃掉了他的大胡子,继续披着神父要人的外衣。一个貌似友善的日本军官为他手下的胡作非为道歉并暂时同意提供保护。但他还是要求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来给日军军官的派对唱歌助兴,当然所有人都知道下场会是强奸或者更糟,由此引发了在此之前肤浅表面、贪财恋物的妓女转而自我牺牲的空前高潮的一幕。
这些社会下层的人当面临生死攸关的当口义无反顾无私奉献之举当然会带来不容置疑的感情和道德的力量,但是过多的关于这个骗局是如何实施的笔墨,无论是从现实世界还是从电影的角度来说都显得不真实不可信,所以结局的可信度和力度都让人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在介绍此片背景时,文章向读者给出了与日本右翼口径一至的数字——“20万”。当然,他同时也指出,此数字存在争议,也有“30万”的说法,不过他放在伤亡数字后的名词并不是people(平民),而是casualties——在字典中的第一条解释为“失去战斗力的士兵”——这也是典型的日本右翼口径,遭屠杀的是混在百姓中的士兵
编后语:看完了《金陵十三钗》国外影评,你是否跟我有一样的感触呢。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美国人还是愿意站在屠杀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因为二战虽然是日本发起的,但美国却多次对日本的平民进行了攻击和屠杀。所以美国在心理上倾向于站在屠杀者的角度进行反思和道德救赎。此前的大屠杀经典影片《辛徳勒名单》和《卢旺达饭店》,片中的英雄都来自屠杀者阵营。而十三钗中的拯救者是被屠杀者自己的自觉行动,这一不同的二战文化心理恐将影响美国人欣赏《金陵十三钗》,并对此片在北美的票房和奖项带来不利影响。